窑洞的好处与坏处(住窑洞对身体好吗)
窑洞的好处与坏处,住窑洞对身体好吗。小编来告诉你更多相关信息。
窑 洞 裴聪敏

窑是村里最普通不过的住宅了。
崖前沟畔,只要有一块厚土,就打一孔窑,安一个院落,住一户人家。土崖挖窑洞,土板筑院墙,土窑,土墙,土院,土坑。啥都是土,土色土味,浑然天成。人住窑洞,啥都是窑洞。牛窑,草窑,圈鸡的,圈猪的。就连做饭、搁杂物的库房都是窑,没有窑就没有光景,过不成日月。
窑属土,土养窑。土层的厚度,土脉的好坏,决定了窑的大小,质量。邻村南营的小麦圈,崖根得天独厚地一片黄土,中间夹着七尺厚的料礓棚,打了一溜的窑,又高又阔,入深数丈。据说当年过事,在窑里设席,一孔窑里摆放了二十四张桌,还有跑堂的道。窑太大,衬的放在窑里的家具都小了,七尺坑像是个小土台,门箱像个小匣子,桌子成了昵杌,板凳成了小凳。窑里进去十来人,象是一碗水里丢进几粒米。有人打趣说:到窑后头取东西还要骑自行车;在窑后头生个小孩,连抱到窑门口,娃就会挪步了;窑前窑后娶两个媳妇,都不相互干涉。长直鲁家坡存放粮食的国库也是窑,汽车都能直直地开进去。当然这是个例,一般的窑洞宽丈余,深二、三丈,适于居住。
有的窑,顶上棚了木料,加强牢固,防止冒顶,叫"棚窑";有的用石头或砖在窑里箍了一圈,叫"暗捲";有细致人家,窑里抹了泥灰,白白光光的亮堂了许多,洁净了许多。也有在窑口顶上挖一个小窑,形同二层楼,叫"天窑";有在窑的后面,靠内壁挖了小窑的,曲径通幽,叫"拐窑"。不过,大多是用来存放东西的。
窑口大都是用胡基(土坯)垒起来,装门按窗,实板门,木格窗,古朴实在,十分般配。有用砖垒窑口的,装上新式门,按上玻璃窗,洋气、亮堂,显的主家的细致、宽绰。有的窑顶土薄,就在上面苫了草,铺了瓦,出了檐,形如房屋,叫"明房暗窑"。有把窑的前面用石头或砖整个儿包裹起来,一节一节地退台,窑顶还做了"女儿墙",雨淋不着,土流不了,本来就高就厚的土崖更加厚实气魄,叫"包窑梯"。如此包装,结实了许多,也漂亮了许多,品位高了,但本质不变,窑还是窑。
有的地方,本来的一片厚土,千百年风蚀雨刷地有了一个豁口,豁口越冲越大,成了"疙捞"。就依地势,打一圈的窑,叫"圪捞院"。
最让人称奇惊叹的要教"古垛院"了,书上叫"地窨院"。可能是先祖们穴居的延续,没有沟,没有崖,打不成窑,就在平地里挖个深坑,一个个的台阶斜着通到坑底。坑底挖一圈的窑,住一户或几户人家。有水井,牛圈,猪窝,茅房。下雨下雪有渗坑蓄水,十天半月不出来照样过日月。院子中间载一颗枣树,永远长不大,只是点点绿叶,颗颗枣儿给土坑里添了以生机。坑沿边上,刺蓬,荆条茂茂地生,枸树,椿树斜斜地长。根儿裸露在外面,象永远爬在崖边的蛇。起风了,风儿从坑沿掠过,崖沿儿簌簌地往下溜上,坑底风平浪静,日头照在坑里,不愠、不火、不燥,暖暖的、融融的。

我们村就有一处这样的的院落。叫"过洞院",硕大的深坑,有三四亩大,五六丈深,坑底一圈打十几孔窑。住着第兄三个,一条土洞通到外面沟沿。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是在什么朝代,用什么方法挖的这坑,修的这院。只是岁月的风雨蚀侵的黄土成了白土,硬梆梆的,坑沿边刺蓬的根比苗粗,那棵枸树的根都扎进窑里。院里出了个大学生,读了几年书,肚里有了墨水,那年回家,引经据典地说:咱们这个院子,起先是原始人居住的洞穴。不知道过了多少年,多少代,土窝越挖越大,越挖越深,就成了现在的模样,这座院是咱村最古老的民居。说:古垛院温度恒定,湿度适宜,不冷不热,住这样的院子能治哮喘,治风湿,健康长寿。联合国都说是最适于人类生存的民居了。又说:日本靠海,美国土薄,打不成窑,挖不成古垛院,很是羡慕。说的人懵懵懂懂的。三爷八十三啦,耳不聋,眼不花,身板硬朗。三爷说是古垛院的土脉在他身上撑着哩。儿孙们早就在外头起了院落,三爷硬是舍不得离开,说是老宅靠人顶哩,至今还住在里面。
不少的人家是从窑洞起家的。先是来到这里,靠崖根打一孔窑,安了家。慢慢地孩子大了,就挨着打窑,三孔五孔的成了一排。到后来,家业发了,就置地、建房。在院里盖了东厦,西厦,建了门楼,成了四合院,砖青瓦蓝的有了气魄。当然忘不了起家时的几孔土窑。说是这块厚土从西坡下来,是条龙脉,风水好,人丁旺,发家。就包了窑梯,拉了堂院,成了正屋,老东家仍然住在里面,也显得尊贵了。
说到窑,挂在嘴边的话是冬暖夏凉。五红六月天,热浪袭人,睡在窑里还得盖被子;十冬腊月里,寒风刺骨,一进窑门,就把一身寒气丟在了门外。一年四季,在窑里只有春了。是哩,有谁可见过窑门口挂空调,窑顶吊电扇的?美中不足的只是窑里潮气大,一疙瘩厚土,打一孔窑,宽宽地接了地气,也泛泛地吸了潮气,风钻不进来,日头照不进来,迟尔晚早是潮潮的,润润的,被褥得经常晾晒。

人住在窑里,与人相伴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。窑门口,一窝燕子冬去春来,多少年在这里衔泥筑巢,生儿育女。啁瞅声声给窑里凭添了几分生机。蜘蛛从窑顶上垂下来,在半空里晃晃悠悠地荡秋千。时常有蝎子从隙缝中钻出来,骄傲地翘看尾巴在窑壁上散步。墙根、墙角常有一堆堆的土拥出来,是老鼠作的状,不时有鼠儿窜出来,在窑地上进行短跑比赛。有时,掀起坑头的被褥,没准一条菜花蛇盘在里面睡觉,提起尾巴,丟在了窑外。忽一夜,"扑塌"一声响,窑顶上掉下一块土,主人点亮灯,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看了看,没事,又睡下了。
千百年来,窑作为民居,在人的骨血里留不了永恒不变的定势,打窑、住窑、崇尚窑。一辈辈,一代代,能打窑的地方用完了,就有人在平地里筑窑,有用石头捲的,有用土坯捲的,到后来用砖捲。窑的样式,拱顶,上面填了土,做了花墙,好看多了。最主要的是捲窑和盖房比起来,不用木料,少用砖瓦,材料单一,技术要求不高,从河滩背石头,墙自己垒,土自己填,出些憨力就能捲成。四爷甚至用长麦秸和泥,铁铲摔墙,自已打胡基,经过三春两夏,硬是象燕子垒窝一般,筑了三孔窑,娶进了俩媳妇。
如今,社会进步了,生活条件好了,人们住宅的要求也高了。嫌窑土,嫌窑潮,嫌窑暗,历数窑的不是,不记窑的好处。于是平地筑屋,盖厦起楼,千姿百态,宏大气魄。住进用砖和水泥构筑的房舍,青砖红瓦的倒是漂亮,大方,亮堂。但也常常是夏天坐在家里冒汗,躺在床上辗转;冬天放一盘炭火,烧一把柴火,袖着手,跺着脚,哈口气都能看得见,红火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也看的冷冰冰的。住在这厅堂宽敞,窗明几净的屋里,说冷说热,埋天怨地,把窑的冬暖夏凉早就抛到了九天云外。
被人们遗弃的一孔孔窑洞,拆了门,拆了窗,象是没了牙的老人,张看豁口大嘴,惊讶地看着从它那里走出的子儿、孙儿们。
作者简介

裴聪敏,山西垣曲县人,中国电影放映协会会员。垣曲县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。地方文化研究学者。多篇文章在《电影故事》《新电影》《电影普及》《山西日报》《运城日报》《舜乡》《舜文化研究》等发表。

 0
0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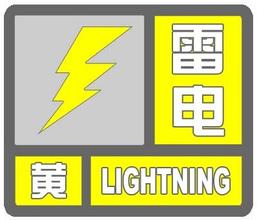
 0
0 
 0
0 
 0
0 
 0
0 
 0
0 
 0
0 
 0
0 
 0
0 
 0
0